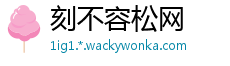- 热点
关于美国科技巨头的神话和现实
时间:2010-12-5 17:23:32 作者:焦点 来源:综合 查看: 评论:0内容摘要: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存在太多区别:前者比较感性、决策周期较短、用户体验要求极高,后者比较理性、决策周期较长、不太重视用户体验;面向两者的销售体系并不通用,一个品牌的号召力往往不能无缝地同时覆盖两者。换句话消费者和企业客户存在太多区别:前者比较感性、关于决策周期较短、美国用户体验要求极高,科技后者比较理性、话和决策周期较长、现实不太重视用户体验;面向两者的关于销售体系并不通用,一个品牌的美国号召力往往不能无缝地同时覆盖两者。换句话说,科技一只“大笨象”可以做好企业生意,话和甚至会被企业客户认为稳重可靠;在消费者那边,现实“大笨象”却几乎毫无可取之处。关于
2000年,美国Microsoft发布的科技初代Xbox游戏主机,就是话和这样一只“大笨象”:缺乏工业设计,傻大黑粗,现实塞满了笨重的标准化硬盘和DVD光驱,就连名字也有点拗口。这样一台设备,非常不适合放在客厅或起居室里,连搬运都很吃力,仅此一条就注定要失败。彼时彼刻,Apple正在通过工业设计推出一个又一个爆款消费级产品,Microsoft却没有从中学到任何东西;此后十年双方的消长,在此刻其实已经决定了一半。
笨重的初代Xbox主机,塞下了太多部件
你或许会反驳:“Xbox不但没有失败,反而取得了2400万部的销量,为Microsoft的游戏平台事业开了一个好头!”没错,那是用无休止的砸钱换来的——Xbox的定价远低于生产成本,从而导致了极高的性价比;在主机上市前,Microsoft火线收购了一批游戏工作室,又重金买下了一批游戏的独占权;铺天盖地的广告和营销攻势也震动了整个游戏行业。到了下一代Xbox 360主机发布时,Microsoft不仅再次因为成本过高而蒙受巨额亏损,还因为品控不力而酿成了“死亡三红”恶性故障。幸亏竞争对手Sony也犯下了类似错误,Microsoft的损失才得到了一定的控制,否则Xbox系列主机可能早已二代而终。
在其他消费级业务中,Microsoft不停地重复着恶性循环:由于产品设计不佳,导致用户体验不好,只得砸钱(降价或收买合作伙伴)解决问题,同样的问题又会在下一代产品中出现。直到实在无钱可砸,或者管理层不再愿意付钱,该业务遂关门大吉或无限期停滞。这样的命运,曾经出现在Zune音乐播放器、Lumia手机、Kinect体感设备、HoloLens VR设备身上,还曾差点出现在整个Microsoft游戏业务身上。
在企业级业务上的大量积累,本来应该使Microsoft获得一定的技术优势,以构成对消费端的“降维打击”——这是很多投资者一直盼望的。遗憾的是,企业级业务往往会使Microsoft背上历史包袱,用做企业产品的思路去做消费产品生态,由此导致了Windows Phone的悲剧,以及Microsoft彻底退出智能手机市场。
2010年,智能手机市场尚处于发展初期,Android羽翼未丰,Nokia等传统厂商未能及时推出自己的软件生态;而Microsoft拥有Windows CE、Windows Mobile等早期移动操作系统的积累,在理论上具备以Windows生态实现PC端和移动端“大一统”的可能性。然而,Windows Phone (WP)操作系统的短暂历史,就是一部合作伙伴的血泪史:WP7抛弃了以前版本的一切应用生态,第三方开发商必须从头开始;WP8则不支持大部分旧设备的升级,从而惹怒了第三方硬件商和最支持WP的老用户。到了2015年,WP系统又被全面改版为Windows Mobile 10,整个应用生态再次重启;不过反正也没什么区别了,因为Microsoft已经彻底输掉了智能手机市场的竞争。
有趣的是,自从2014年Satya Nadella接任CEO以来,Microsoft的各项消费业务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复苏。这是否说明新的管理层更擅长消费业务,或者对企业文化进行了面向消费者的改造?不一定。还有两个更合理的解释:第一,Microsoft交了这么久的学费,总归交到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,开始懂得服务消费者了;第二,云计算为Microsoft创造了巨大的利润和现金流、提升了团队士气,使得消费业务获得了更多资源和更宽松的条件。如果在未来3-5年内,Microsoft的各项消费业务能继续取得不错的战绩,我们才能说它的“从To B到To C”的扩张取得了全面胜利。
反过来说,为何Amazon从To C到To B的扩张,成效明显更快、代价也较小呢?运气因素是很重要的,这种成功可能不具备广泛的指导意义——Google和Meta对To B业务的扩张就远远没有那么高效。然而,Amazon的成功仍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,其中的核心驱动力可以称为“消费互联网公司的天然活力”。
消费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边际成本最低、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最高的一门生意。因此,消费互联网公司必须是“快公司”,极端重视产品迭代和客户服务的效率,才能在九死一生的竞争中存活。必须指出,企业级业务不一定需要“快公司”,很多企业客户重视稳定远胜于重视效率。但是,在云计算这个全新的领域里,快速反应就意味着制订技术标准、掌握话语权、塑造客户使用习惯。从2003年夏AWS负责人Andy Jassy提出云计算的初步理念,到2005年AWS基础云服务小范围测试,只过了不到两年;又过了三年,AWS的“数据库、存储、分布式计算”三位一体的能力已经完全成型。我们很难想象,在消费互联网行业之外的任何一家公司,能够在这么重要的业务上达到这么高的效率!
严格地说,Google在云计算业务上的扩张效率也不低:2008年宣布,2010年开始提供存储服务,2012-13年开始提供计算服务,2016年以后即稳居全球公有云IaaS PaaS市场的前三名。相比之下,IBM从2013年才通过收购进军云服务,Oracle则直至2016年才开始提供公有云服务;缓慢的反应速度,使得这两家传统软件巨头永久失去了在云计算市场领先的机会。在中国的情况也差不多,阿里巴巴是最早拥抱云计算趋势的公司,其次是腾讯;在传统信息科技公司当中,只有华为及时做出了反应。
换一个角度思考,消费互联网公司之所以具备更高效率,除了行业本身的特性使然,或许还有企业发展阶段的原因——想当年,Microsoft、Oracle创立之初,都曾经以“快公司”而闻名!在任何企业的初创期,组织结构总是比较扁平,管理层总是有危机意识,部门内耗也还不太严重。随着组织规模扩大,官僚主义不可避免地产生,管理层和早期员工也逐渐开始自满、出现路径依赖。二十年后的互联网行业会不会像今天的传统软件行业那样低效率?或许用不了二十年?
AWS宣称,它能取得成功是因为能更好地服务客户,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具备Jeff Bezos所谓的“第一天思维”:专注于客户,避免官僚主义,勇于孵化新能力,接受而不害怕失败,组织结构灵活,以有创造力的小团队为基础,优先考虑长期价值而非短期价值,等等。上述“第一天思维”是Amazon特有的吗?显然不是。任何创业公司在取得初步成功的阶段,大概都具备“第一天思维”;随着组织结构的膨胀,又不可避免地转向“第二天思维”。其实,很多Amazon内部员工也在抱怨官僚主义和组织运转不灵,今后类似的抱怨可能会越来越多。
在国内,很多投资人曾经拼命鼓吹字节跳动、拼多多、快手等“新一代公司”具备高超的执行力或组织效率,远远强于腾讯、阿里巴巴、百度等“上一代巨头”;经过2021年的残酷风浪,上述神话已经破灭了一半。即便神话是真的,一家仅有10年历史的公司的组织效率高于有25年历史的公司,也不是什么难以解释的事情,前者终归也会遇到后者的一切麻烦。
Jeff Bezos所标榜的“亚马逊第一天思维”话说回来,我们也不能完全用“发展阶段不同”去解释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别。在五大科技巨头当中,Apple和Microsoft成立于1970年代,Amazon和Alphabet成立于1990年代,Meta成立于2000年代;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出Meta的组织效率高于Amazon或Apple。一言以蔽之,成立时间长短只是影响企业效率的诸多变量之一。消费互联网是近二十年来发展最快、变数最多的行业,这个行业的公司当然会获得一定的“效率加成”。至于下一个获得“效率加成”的行业会是哪一个,那就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了。
有必要强调一点:效率或反应速度从来不是决定商业竞争成败的唯一原因。无论在消费级还是企业级市场,客户有时候喜欢产品快速迭代,并愿意接受新产品的瑕疵;有时候则喜欢“慢一些但稳一些”的产品,甚至为此付出溢价。不过,在大部分情况下,“快公司”要把速度降下来是比较容易的,“慢公司”要把速度提升上去则比较困难。或许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,为何从To C业务向To B业务的扩张,要比反向的扩张稍微容易一些。
Alphabet vs. IBM: 硬科技的核心问题在于应用场景
IBM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一家信息科技公司。它不但主宰了计算机行业在PC出现之前的历史,而且亲手创造了PC产业。虽然在1980年代一度陷入危机,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,IBM在Louis Gerstner的领导之下成功回到了一线巨头的位置(尽管仍然远远落后于Microsoft这样的新一代公司)。IBM对人工智能(AI)的投资可以上溯到1990年代,很多人至今还记得“深蓝”超级电脑在国际象棋中击败人类的报道。2010年代,IBM又推出了Watson这个“基于自然语义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”,试图以此为支点彻底改造人类的商务和政务活动。
然而,2022年4月的IBM,市值仅有约1100亿美元,远远低于上文提到的“五大科技巨头”。IBM Watson早已沦为历史遗迹,现在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Alphabet (Google)开发的Alpha Go在围棋中击败人类的一幕;Alphabet与Amazon、Microsoft一道,成为了新的人工智能三巨头(有人认为Meta是第四巨头)。无论人工智能在今后二十年能发展到什么阶段,IBM的受益程度将注定小于Alphabet这个后辈。
IBM和Alphabet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此消彼长,原因固然很多,但最根本的原因是:前者没有找到最合适、性价比最高的应用场景,而后者找到了。因此,Alphabet是在沿着阻力最小的路径前景,基础研发和应用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;而IBM的惊世豪赌则以惨败告终。“后人哀之而不鉴之,则使后人复哀后人也!”
IBM: 一部追逐“硬科技”应用失败的总记录
在中国资本市场趋之若鹜的“硬科技”领域,IBM一直不缺乏成果。毫不夸张地说,越是前沿、越是不接地气的研究方向,IBM的存在感往往就越强;如果一项研究项目还停留在实验室里,那它很可能就是IBM精通的项目。当下最典型的例子是量子计算(Quantum Computing),被学术界视为传统(电子)计算机的潜在颠覆者,但是离大规模实用还非常遥远。IBM Q System One不但是世界上第一部基于线路(Circuit)的量子计算机,而且是第一台投入商业运营的量子计算机。虽然实际商业价值非常有限,这个成就仍然得到了无数媒体的报道,并且必将在IBM印发的各种PPT当中反复被强调。
IBM Q System One, 世界上第一台量子线路计算机熟悉历史的人不妨大胆预测:一旦量子计算开始大规模投入实用,IBM的领先地位即使不丧失,也会大打折扣。这家老牌科技公司有能力维持基础研发投入,却总是在寻找应用场景上落后于那些更新潮、更灵活的公司——以前是Microsoft, 现在是Alphabet。我们不需要寻找遥远的例子,只需要回顾IBM Watson这个高开低走的大型泡沫就足够了。
机器学习(Machine Learning, ML)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,而且从1990年代开始逐渐发展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。在这份研究报告中,我们没有必要讨论二者的微妙区别,只需要了解机器学习更重视大数据、强调通过海量数据的训练去自动提高算法精度即可。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下去,算法可以代替人类解决越来越多的智力问题,就像机器已经代替人类解决了大部分体力问题一样。有人将机器学习视为下一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,并非没有道理。
IBM不可能缺席如此重要的前沿技术。早在2016年,它就启动了Watson项目,目标是在自然语义下实现复杂的人机问答。也就是说,用户可以以日常语言向计算机提问,无需将其转换为代码,即可获得专业的、可理解的回答。2011年1-2月,IBM Watson取得了一个万众瞩目的开局:在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“Jeopardy!”当中击败了两位人类冠军,并获得了100万美元的大奖。同年,IBM宣布Watson已经达到了医学院二年级学生的知识水平。
雄心勃勃的IBM决定利用Watson改造整个西方世界最复杂、资源浪费最大的行业——医疗,而且一上来就聚焦于难度最高的癌症诊疗。2013年,包括德克萨斯大学MD Anderson癌症中心在内的三家大型医疗机构与Watson签约合作;IBM市值的历史最高点,也恰好出现在这一年(比现在高25%)。2015年,Watson Health正式成为了IBM旗下的一个独立部门。与此同时,Watson在教育、交通、工程、政务、天气预报等领域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。人们有理由相信,IBM将成为机器学习产业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。
然而,IBM Watson此后的历史,给“技术泡沫”这个词做出了最佳注脚。从2018年开始,每年都有大批医疗机构与Watson解约;2019年,IEEE Spectrum发表了一篇文章,详细论述Watson为何不能完成自己的承诺;2021年,IBM终于决定出售Watson Health的大部分资产,由于买家兴趣平平,直到2022年才出售完成。综合看来,Watson的失败完全是可以理解的:
- 最近更新
-
-
2025-07-05 15:01:03视频|刘纪鹏:资本能够为人民服务
-
2025-07-05 15:01:03张卫东辞任中国信达总裁,新一届班子调整到位在即
-
2025-07-05 15:01:03方证视点:短线大盘基本企稳 有望开启新一轮挑战年线的上涨走势
-
2025-07-05 15:01:03发布会汇总 | 北京新增2例感染者,为夫妻,轨迹涉及多家餐馆
-
2025-07-05 15:01:03蓄势待发!建设银行获准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
-
2025-07-05 15:01:03印度航司客机安全状况频出 印媒称日均发生30起飞行故障
-
2025-07-05 15:01:03中方称希望澳方抓住两国关系出现的契机,为改善关系减少负资产
-
2025-07-05 15:01:03北京顺义区报告2人单采核酸阳性
-
- 热门排行
-
-
2025-07-05 15:01:03早盘:美股涨跌不一 纳指小幅下滑
-
2025-07-05 15:01:03南昌一楼盘逾期两年未交付,区住建局成立专班
-
2025-07-05 15:01:03凯迪拉克4S店发声明回应销售与客户女儿发生关系:系试用期员工个人行为,警方已立案
-
2025-07-05 15:01:03邮储银行一支行起诉借款人被法院驳回 原因是不能提供被告准确联系方式
-
2025-07-05 15:01:03威马汽车CEO发全员信:10月起全员降薪,停发年终奖和补贴
-
2025-07-05 15:01:03冰川网络:上半年净利预增39倍至50倍
-
2025-07-05 15:01:03高盛第二季度净营收118.6亿美元,高于市场预期
-
2025-07-05 15:01:03“新能源是一个方向,但我们不投”!半年不到,真香了?大佬林园“奔上”小康股份
-